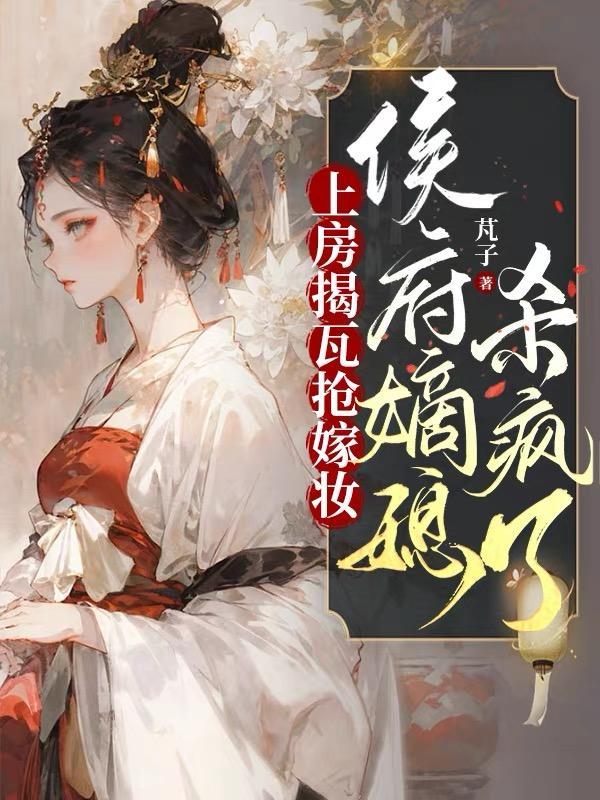乐趣小说>丑女开局,逆袭国色天香 > 第157章 阿陵你有小两月身孕了(第2页)
第157章 阿陵你有小两月身孕了(第2页)
因为“贪污”一事至今仍未平反,所以聂成永的真实身份也就掩藏至今。
“聂家算是欠了康家的情,老爷子虽表面不提,但心里是看重四郎主的,他人又老实本分,这些年来勤勤恳恳,昭玉夫人心里也都清楚着。只是众人不好提及罢了,毕竟那事到现在还是禁忌。”
“原先我们还当四郎主身子不好,是常年庄子上跑积劳所致,昭玉夫人还让他不必再操劳,是他自己总觉得不妥,说要做些事才安心。”
“就这样一个好人,不想竟——”房媪说起来颇痛心。她是府里的老人了,所有事情不仅是知晓,也都是经年累月看在眼里的。
桑陵也知道她藏在后面的话,是在怨恨被那一对狗男女害了。
所以说聂广那人多可怖,聂成永又有什么地方威胁到他了?偷了人家媳妇不说,还帮着下药毒害。
不过聂广的结局,如今看来依旧不明朗。也不知道那日他们几人在是非堂谈到子时,昭玉夫人是如何说的。
桑陵想,她这个婆婆在这事上也该要硬气些了,连带合卺酒的事一道说了,数罪并罚,就算聂太公不可能杀了聂广,总也该要有些落到实处的处罚了。
一刻钟后高恒出来开药,府中侍医就在一旁记着,桑陵候在边上,也没有说什么。
好在表哥也不是个爱打探的人。
随后又领着他去了趟午苑——为成媪看看,一路问了问姑姑近况,再问了问他。
“母亲在家安好,我前几日再去了趟回阳,虽时疫已经退散,但其实——”他顿了顿,“其实也还是死了不少人的。”
桑陵敛容沉默少倾,跟着喟叹,“世事无常,但愿他们下辈子投身好人家,不必再遭受这样的苦难。”
高恒听后也只是无话,等到了午苑院门前,他才停了一脚,桑陵见他停住,于是也停住了,不禁疑惑回望。
“脸上的伤。”高恒昂询问。
她便用手摸了摸,也都恢复了有几日了,起先几个夜里,成媪和卫楚会轮番用冰块给她敷,第三日就消了大半的肿,不细看也看不大出来,现在就颧骨下还有一点青紫,夜里也都会用热毛巾敷一会。
高医生还是眼尖的。
她低眉沉吟,也不打算隐瞒,“是被打的,不过是我自己打的自己。”深吸了口气,复抬眸看他,眼底含着宽慰的笑意,“这里头的事要解释起来有些复杂,总之我不是受了欺负就是了。”
高恒回味了会话里的意思,也就知趣不追问了,不过末了还是提了提,“手边备了红花油没有?”
桑陵点头应声,“放心罢表哥,就是我不记得,成媪也会留心的。”
成老妈妈是比她自己还要看重她外貌上的保养。
高恒无奈笑了笑,随后入堂屋帮成媪听脉,开方子的时候已是未时。
“倒没什么大碍了。”他说,“只是今后行动间注意些,少弯腰弓背的忙活,也避免久坐。”
成媪见着旧主也高兴,脸上一直含着笑,又说,“少主既然都来了,也请为我们夫人听听平安脉罢。”
于是乎,高医生又留了一小会。
仲春时节的微雨淅淅沥沥打在廊檐上,溅起的水花染白了廊下一线,庭前蕉叶也垂下一片来,正遮住了前堂室内的光线,里头的声音也都被压住了似的。小原杏端了茶盘从回廊过来。
里头泡着的可是上月从蜀地献上的茶叶。莫说午苑里头了,就连侯府都是头一回拿出来招待人。
她碎步到堂前跪坐,同屋内的晏瑶交接茶碗,第二杯刚奉进去,就听里头的声音,“阿陵,你有小两月身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