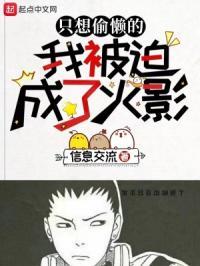乐趣小说>悬案侦破之谜 > 第203章 暗夜疑云第3章(第1页)
第203章 暗夜疑云第3章(第1页)
办案人员不动声色,随即展开细致入微的调查工作。
他们多方走访、调取监控、查阅交通记录,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与案件相关的蛛丝马迹。
经过严谨缜密的排查核算,他们现从邯郸峰峰矿区的案现场开车到菏泽,路途遥远,按照正常车与路况,最少需要4个小时。
而案时间是13号凌晨3点左右,高明全却声称当天早上6点钟自己就已经和两个工友一起去干装修了。
并且那两个工友在接受询问时,都信誓旦旦地证实了他的说法,描述当天见面的场景、出的时间以及干活的细节都极为详尽,没有丝毫破绽。
不仅如此,高明全的儿子高庆兴也及时提供了有力证据。
他皱着眉头,神情略显疲惫又透着几分焦急,向办案人员讲述道:“岳父出事没多久,我这边还正一头雾水呢,妻子小芳就打来电话,语气里满是怀疑,一口咬定是我们高家人干的。
我当时又气又急,为了证明清白,当即就拍了照片给小芳。”
说着,他拿出手机,翻出那张照片展示给办案人员看,照片上,高明全和高庆兴正躺在床上酣睡,被子随意地搭在身上,床头摆放着的闹钟、水杯等物件清晰可见。
从房间的布置到人物的状态,种种细节综合起来,都能确凿无疑地证明当时父子俩确实在菏泽的家里,处于熟睡之中,根本不可能跨越漫长的距离,出现在邯郸的案现场。
办案人员仔细端详着照片,比对时间戳与相关细节,陷入了沉思,案件似乎陷入了一团迷雾之中,真相愈扑朔迷离。
原本随着对高明全调查的逐步深入,线索如同紧绷的丝线,一根接一根地断掉,案件毫无预兆地陷入了僵局,仿若一辆风驰电掣的刑侦列车猛地撞进了一堵无形且厚实的墙,被迫停滞不前。
刘元河躺在病床上,即便伤痛已将他折磨得虚弱不堪、面容憔悴,可每次提及案那夜的惊魂场景。
他眼中都会燃起笃定的火焰,坚称凶手就是亲家公高明全,言辞恳切,不容置疑,那是从生死边缘挣扎回来烙印在心底的认知。
然而,所有摆在眼前的客观证据,却似一道道坚固的壁垒,严严实实地封住了这条看似明晰的追查路径——交通行程数据冰冷地显示着从案现场奔赴菏泽所需漫长的4个小时。
工友言之凿凿的证词、高庆兴那带有时间戳且细节满满的照片,无一不在佐证着高明全没有作案时间和实施犯罪的可能。
在这矛盾重重、迷雾弥漫的局面下,一个尖锐且亟待解答的疑问,如同阴魂不散的幽灵,在办案人员的心头盘桓:
如果不是高明全,那真正隐藏在黑暗中、手持利刃、对刘元河痛下杀手的凶手又会是谁呢?
就在办案人员围坐在堆满卷宗的桌前,眉头紧锁、苦思冥想,反复梳理着每一条细微线索。
试图从错综复杂的信息迷宫里寻出一丝曙光之际,案两天后的四月十四号深夜,一阵急促且带着哭腔的电话铃声骤然打破了办公室里令人窒息的寂静。
电话那头,秀芬的声音颤抖得厉害,焦急与恐惧如同汹涌的潮水,顺着电波倾泻而来,她说医院里出现了两个奇怪的陌生人,那两人突兀地现身在病房所在楼层,神色匆匆、形迹可疑,一开口便自称是来探望刘元河的。
可当秀芬满心狐疑、准备带着他们前往病房时,还没等见到刘元河本人,这两人仿若惊弓之鸟。
不知被何种莫名的因素触动,竟匆匆转身,沿着走廊快步离开,身影迅消失在转角,那仓促离去的姿态,就像生怕被人抓住把柄、识破身份一般。
办案人员接到电话后,丝毫不敢耽搁,警灯闪烁、警笛呼啸,风驰电掣般赶赴医院。
然而,抵达时,那两个神秘人早已没了踪影,只剩空荡荡的走廊,灯光惨白,映照着办案人员满是忧虑与急切的面庞。
他们并未气馁,迅找到当晚值班护士,那护士是个年轻姑娘,此刻仍心有余悸,脸颊还带着几分受惊后的苍白。
手不自觉地抚着胸口,眼神中满是紧张与不安,向办案人员讲述起当时的情景。
“那两人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大半夜的,医院本就安静,他们走路没什么声响,可那身形看着就不像是普通的探病家属。”
护士微微皱着眉,努力回忆着细节,声音虽还有些颤,却条理清晰,“他们穿着深色的衣服,连帽子都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眼睛,看不清长相。
走到护士站这儿,问我刘元河住哪个病房,说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还带着点外地口音,语气特别生硬,不像是真心来探望病人的,倒像是在打探什么。”
办案人员一边认真记录护士的话,一边敏锐捕捉其中关键信息,目光中透着犀利与决然。
誓要从这看似细微的线索里,挖掘出破解案件僵局的关键突破口,揪出那潜藏在暗处、蓄意制造罪恶的真凶。
在那个静谧得让人有些毛骨悚然的深夜,医院的走廊被惨白的灯光涂抹得如同一条冰冷的通道,时间悄然定格在十一点半左右,大多数病房都沉浸在梦乡的静谧之中,唯有值班护士台还透着一丝昏黄的光亮。
就在这时,一男一女如同两个幽灵般悄然闪进了医院的大门,脚步匆匆却又透着一种刻意压抑的谨慎。
每一步落下都轻得近乎无声,仿佛生怕惊扰了这沉睡的夜,可这种不合时宜的小心翼翼,反而让他们显得愈突兀、格格不入。
那女子身形苗条,却裹在一件宽大且深色的风衣里,衣领高高竖起,几乎要遮住大半张脸。
仅露出的一双眼睛,还被严实的口罩严严实实地遮蔽,只留下一道狭长冷漠的视线,让人难以窥探其真实面容与表情。
她紧紧跟在男子身旁,微微弓着身子,像是在躲避着什么无形的威胁,又像是急于隐匿自己的存在。